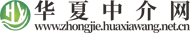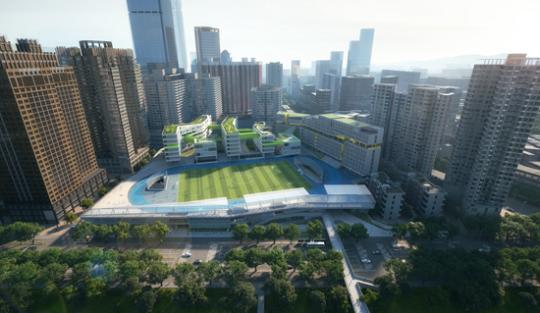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潮新闻客户端 陈建新
虽然我的小学和初中有不少语文老师,但我印象深刻的只有两个,小学的张老师和初中的王老师。我对文学和语文的兴趣,起源于我家边上的小书摊,但强化这个兴趣,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我的两位语文老师。
小学三年级,一位新语文老师到了我们班。老师姓张,其实也不“新”,他当时的身份好像还是代课老师,但在之前已经教过比我们高一届的同学,口碑很好。他同时兼任我们班的班主任。张老师长得高而瘦,脸很白净,说话细声细气,温文尔雅,他的语文课很受同学们的欢迎。
小学三年级我除了看小人书,看中国少年报,还阅读我妈妈个人征订的《人民文学》,三年级结束后的暑假,我妈妈从工厂图书馆借来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那是因为我在我家附近的小河里玩水,不小心让河底的一件破铁器扎破了我的脚板,一个形状像小嘴的伤口让我下不了地,整天只能无聊地坐在家门口看风景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读长篇小说,看完这部小说,我的课外阅读打开了新天地,接着读了不少从邻居和同学处借来的长篇小说。这些小说的情节吸引着我,人物感动着我,还有那似懂非懂的爱情描写也让我激动。在这种随意的阅读中,我认识的字和词语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教科书,估计我的作文也受到了影响。
张老师来了不久,很敏锐地发现了我,我写的几篇作文让他很赞赏,好几次在语文课上公开表扬我。四年级时,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参观杭州市少年宫一个展览,参观完毕,少年宫要求我们写一篇观后感当场交稿。张老师“钦点”了我和另外一个语文成绩也很不错的女同学留下来写观后感。四年级的男女生已经开始互相“避嫌”,我居然不和这位女同学商量,略作思索,拿起笔就在本子上写了起来,大概不到20分钟,完成了这篇观后感,交给少年宫的老师。本来以为完成任务就没事了,没想到在一周后的语文课上,张老师说,我们班的这篇观后感得到了市少年宫老师的好评,整篇观后感居然没有一个错别字,这在少年宫收到的小学生观后感中,是很少见的。这个课堂表扬,让我自信心爆棚,越发对语文发生了兴趣。很可惜,文革的爆发,让我在小学五、六年级时处于失学状态。但我的阅读兴趣不减,“停课闹革命”的两年中,我除了主动向家里要求的喂养鹅鸭外,就是到处借书看。有时候我还会溜到街上,阅读各种大字报。有一次我去武林门车站送在南浔工作的小姨,回家没坐公交车,而是步行沿着延安路往南走。记得在浙江医科大学的大围墙下,看到一长溜大字报,我从北到南把每一篇大字报都仔细读了一遍,回家迟了两个多小时,把在家等我的外婆急得要死。
资料图。CFP供图。
1969年的春天,我终于进入了初中。当时除了极少一两个同学不再继续读书,大部分小学同学都一起升入初中。初中是刚办不久的新学校,名叫江干中学,与南面的江滨中学和北面的江城中学构成江干区中学的“三江”中学。因为是新办中学,学校的教育质量不高,有些老师甚至连大学文凭都没有。好在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,社会对学习不看重,对文凭也不重视。所以我入学后各科成绩虽然在班上名列前茅,但并没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特别关注,只是到期末考试时,班上那些顽皮同学才会与我相约,考试完毕给他们扔纸条。我在这种时候并无原则性,只要有人要,我就会答应,反正学校和老师对此都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让我和班里的“好汉们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
初二开学时,换了一个语文老师来当班主任,后来才知道他刚从杭大中文系毕业,把比我们高一届的“两届生”带毕业。老师姓王,性格很“扭”,喜欢与人顶牛。每当和女生谈话,他总是别着脖子不看女生,谁要是在他面前表现很嗲(很多女生对男老师总是会拿出这样的“看家本领”,很多时候效果不错),一点都没用,因为王老师不吃这一套。他这样的做法反倒颇受男生们的赞许。他开课后,发现我的作文不错,多次把我的作文拿到课堂上朗读。有一次,他布置的作业是写诗,收到我们的作业后,他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大声朗读了我写的诗歌。其实我当时能够读到的诗歌就是报纸上类似郭小川、贺敬之式的革命白话诗,内容直白,不绕弯弯,写得好不好就靠语言的流畅和押韵,我这首诗大约就是在这两点上达到了他的要求。然而,他当堂夸奖后,却激发起我写诗的热情,下课后专门到他寝室讨教,他的建议是多读一些好诗,并没有更深入的指导。我问他哪些诗是好诗,到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好诗,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。我当时有些不理解,也不太满意他那种不把话说透的表达。直到很久后我才明白,王老师那时候哪敢真正辅导我,因为彼时正在揪阶级异己分子,好像不久后还掀起一打三反运动,我们一位体育老师被揪上台批斗,他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年轻老师,哪敢对学生“放毒”?对我的提问,他只能打哑谜了。但王老师对我的鼓励却在我微薄的文学兴趣上添薪加油,更加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情,以及寻找各种文学作品阅读的强烈兴趣。
我的可怜的两年半初中生涯,教科书里只有两篇古文,一篇是《愚公移山》,另一篇是《三元里抗英》,所谓古典诗词,只有毛主席诗词。我通读毛主席诗词时,才算间接读到陆游的《咏梅》和柳亚子的那首呈送给领袖的七律“开天辟地君真健,说项依刘我大难”。柳亚子的诗用典太多,难懂,也没有引起我背诵的兴趣,但陆游的这首词却被我背得很熟。后来我从一位邻居(一位业余工人作家,曾经在杭报等报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)那里听他说起唐诗宋词,还当场用抑扬顿挫的山东普通话朗诵李白的《静夜思》,让我对古典诗词有了更强烈的兴趣。进工厂当学徒后,我才读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诗歌,也读到了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拜伦、雪莱、济慈、歌德、席勒等外国诗人的佳作。
从今天我一个七十老翁的眼光看,我的两位语文老师对我的激赏,是我对文学和写作感兴趣,一步步与文学结缘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如果没有碰上这两位语文老师,就没有我后来的考上大学中文系,当然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名中文老师。这样的经历令我与今天很多高中语文老师有共识:一个好的语文老师,不是把教材里的内容讲得如何好,而是如何激发学生对语文和文学的兴趣。一篇课文,无论你讲解得如何到位,都不能代替学生自己的阅读和理解。所以,相比之下,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要。而在这个过程中,需要你与学生的交流和引导。像我这样,几十年后已经把老师在课堂的讲课内容忘得精光,却记住了老师对我的夸奖与鼓励,可见后者的重要性。
关键词: